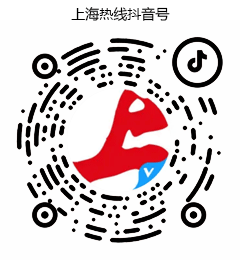帕金森病:从个体困境到治疗困局的突围之路
“每次吃完药,我妈能利索1小时,手脚不抖、能活动,其他时间基本卧床。她看不懂电视,也不会用智能手机,很少说话,即便开口也含糊不清,就这么坐着发呆。”76岁的李奶奶患帕金森病20余年,女儿晓蕊说起母亲的状况,语气平静却藏着化不开的忧虑:“我外婆也是这病,现在轮到我妈,有时候真怕自己将来也会这样。”她轻声补充,“如果将来妈妈能不遭罪地走,对她来说或许是种解脱。”
37岁的晓军半年前发现右手像“搓药丸”似的抖,胳膊抬起来变慢,走路时胳膊也甩不起来。当医院初步诊断为“帕金森病”时,他脑子瞬间懵了:“这不是老年病吗?是不是搞错了?能治好吗?”医生开了一个月的药,说帕金森病患者对左旋多巴类药物通常有反应,“我现在就盼着吃药没效果——不是这病,那该多好。”
帕金森病是一种以多巴胺能神经元死亡为核心的退行性疾病,也是第二大常见神经退行性疾病,仅次于阿尔茨海默病(老年痴呆症)。据了解,全球帕金森病患者已超600万人,我国大概占50%。在60岁以上人群中,帕金森病的患病率约为1%—2%,80岁以上人群可达4%—5%。一方面,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患病率呈上升趋势;另一方面,随着疾病的进展,帕金森病的运动和非运动症状会逐渐加重,不仅会损害患者本身的日常活动,也会带来巨大的社会和医疗负担。
诊断:没有“金标准”的迷宫
“吃了五天左旋多巴,症状一点没改善。”晓军的困惑,道出了帕金森病诊断的复杂性。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刘疏影解释,对左旋多巴的反应确实是确诊的重要依据——帕金森病的核心是脑内多巴胺不足,这源于黑质致密部的α-突触核蛋白错误折叠、沉积,导致40%-50%的多巴胺能神经元不可逆死亡,最终使纹状体多巴胺水平下降80%以上。“补充多巴胺能缓解症状,本是疾病的‘特性’。”
但确诊远非“吃药有效”这么简单。目前,帕金森病没有单一生物标志物(如特定血液指标或影像学结果),诊断靠临床综合评估:核心运动症状需满足至少2项(必须包括运动迟缓),比如“搓药丸”式静止性震颤、“铅管样”或“齿轮样”肌强直、动作变慢等;非运动症状(嗅觉减退、长期便秘、睡眠障碍、情绪或认知问题)也会作为参考。此外,症状是否逐渐加重、对左旋多巴是否敏感,都是关键依据。
“黑质超声正常,不代表没病。”刘疏影强调,包括黑质超声、头部MRI、PET/SPECT(测多巴胺转运体功能)在内的检查,多是为了排除其他疾病,而非直接确诊。缺乏“金标准”的根源,在于病因和病理机制尚未完全明确:疾病早期(前驱期),患者可能仅出现嗅觉减退、抑郁、失眠等非运动症状,因无典型运动症状无法确诊;直到病理损伤累及中脑黑质,出现震颤、强直等症状时,病程已进入Braak分期3期,早期干预窗口早已错过。
因此,当出现典型非运动症状时,就应该引起高度重视。早发性病例进展相对缓慢,且对药物反应较好,早期识别和干预可显著改善生活质量。
调药:没有“万能处方”的个体化博弈
《中国帕金森病治疗指南(第四版)》指出,帕金森病的治疗原则是综合治疗、多学科治疗模式和全程管理,以药物治疗作为首选并贯穿整个治疗过程,结合手术治疗、运动与康复治疗、肉毒毒素注射、心理干预与照料护理,长期管理,长期获益。
目前临床常用的帕金森病治疗药物共有6大类,包括左旋多巴制剂(如多巴丝肼、卡比双多巴)、多巴胺受体激动剂(如盐酸普拉克索、盐酸罗匹尼罗)、单胺氧化酶抑制剂(MAO-B)(如甲磺酸雷沙吉兰、甲磺酸沙非胺),儿茶酚—O—甲基转移酶(COMT)抑制剂(如恩他卡朋、托卡朋)、抗胆碱能药物(盐酸苯海索)和金刚烷胺等,同一类药物具体到每位患者的用法、用量会因症状不同而有所差异。
李奶奶如今每天吃4次药:早6点、10点、下午2点和6点,每次1片多巴丝肼(左旋多巴制剂)加0.375毫克盐酸普拉克索(多巴胺受体激动剂)。“这20多年,药量和次数越调越多。”晓蕊说,母亲六七年没去过医院,药效差了就问病友,却不敢照搬别人的方子,“怕吃错了更糟”。
“千人千帕,别人的处方可能是你的‘毒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许二赫的话,点出了帕金森病调药的核心难题。同为帕金森病,症状轻重、进展速度、身体耐受度千差万别,用药自然没有“万用公式”。
更棘手的是疾病进展带来的“治疗窗危机”。许二赫解释,早期药物效果平稳,但随着大脑“缓冲”多巴胺的能力衰退,左旋多巴(半衰期仅1.5小时)的短板逐渐暴露:受损脑细胞无法储存、稳定释放药物,导致“治疗窗”极窄——药量不足时(“关期”),患者突然僵直、动弹不得;稍过量(“开期”),又会不受控制地乱动(异动症)。药效像“过山车”,波动越来越频繁。此时,左旋多巴单药就显得不够了,药物调整以延长无异动症的开期十分重要。
“一般来说,往往是在早期患者中,可能会优先考虑使用长效制剂,如多巴胺受体激动剂(缓释片)或单胺氧化酶B抑制剂。”许二赫表示,这种用药策略可以推迟或减少使用左旋多巴,从而延缓运动并发症(如异动症)的出现。“帕金森病管理得好,不会影响寿命。前提是医患充分沟通,制定长期规划。”
新药频出,为何仍陷“缺药”困境?
2025年5月底,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陈彪教授团队开出全国首张甲磺酸沙非胺片处方。“作为第三代MAO-B抑制剂,它既能抑制多巴胺降解以延长药效,又能阻滞离子通道减少谷氨酸过量释放,改善神经元过度兴奋,进而改善一系列非运动症状,为帕金森病患者的治疗带来了新的选择。”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毛薇说。
但不断涌现的新药,并未终结“缺药感”。毛薇坦言,当前治疗有三大痛点:一是药效“过山车”——大脑无法缓冲多巴胺,患者在“僵住不动”(关期)和“乱动”(开期)间反复切换;二是异动症难防——长期用药后,不受控的扭动可能比原发病更影响生活,且限制药量调整;三是非运动症状(如失眠、便秘)控制不足,同时缺乏更便捷的给药方式(如长效注射剂)。
更根本的局限在于,现有药物都是“对症治疗”,能缓解症状却无法阻止神经元死亡。“我们最期待的是‘疾病修饰治疗’——不仅改善症状,还能修复神经元、延缓进展。”毛薇说,这或许是打破帕金森病用药困局的关键。
从诊断的迷雾到调药的博弈,再到药物的局限,帕金森病的治疗始终在“与时间赛跑”。而解开这场困局的钥匙,既藏在个体化治疗的精细里,也藏在对因治疗的科研突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