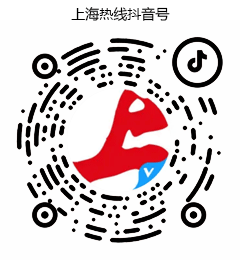从秦代的“六甲五方”看新见秦刻石文字
侯方良、仝涛相继于青海玛多扎陵湖北侧尕日唐发现的很可能属于秦代遗存的石刻文字资料,其真伪引起争论。《汉书·食货志上》有关于童蒙教育的记述:“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所谓“书计”,是说基本识字计算能力的培养。而“六甲五方”,顾炎武说:““六甲”者,四时六十甲子之类;“五方”者,九州岳渎列国之名。”(《日知录》卷二七《汉书注》)也就是说,“六甲”是关于时间的知识,“五方”是关于空间的知识。通常都将这段文字理解为汉代教育史料。然而班固下文说:“此先王制土处民,富而教之之大略也。”周寿昌也说:“此《礼记·内则》之言。”反映的是“古人小学之所有事”(《汉书注校补》卷一七《食货志第四上》)。我们如果以秦代人涉及“六甲五方”的知识结构为视角,应当有益于对新见秦刻石文字的理解。
新见秦刻石的历日问题
有关这处秦刻石异议产生的焦点之一,是最初发表时的释文“廿六年三月己卯”问题。
如刘钊所说,“根据最新的高清照片,可以说“廿六”是“卅七”的误摹已成定谳”。于是,“历日问题的疑难”“涣然冰释”。“检饶尚宽先生编《春秋战国秦汉朔闰表》,秦始皇三十七年三月朔戊寅,初二日即为己卯,所以五大夫翳在扎陵湖山上刻石的具体时间可以确定为秦始皇三十七年三月己卯日,即公元前210年3月27日。”(刘钊:《再论昆仑石刻》,《光明日报》2025年6月30日08版)
其实,仝涛起初采用的就是饶历。但是有的古历法研究专家以为“饶历是有问题的”。如饶尚宽“推算并采用了“年中置闰”的历谱”,“至少目前看来,是缺乏史料根据的。”(曲安京:《“廿六年三月己卯”与〈颛顼历〉不符》,《光明日报》2025年6月30日08版)也就是说,“历日问题的疑难”,现在也许还不能说已经“涣然冰释”。
不过,“历日问题”的解决固然可以使得我们能够完整准确地理解石刻文字内容,但“历日问题”的存在,却并不能简单地作为判定伪刻的证据。
就我们对秦汉石刻资料的知识而言,文字标记出现时间错误,其实并不罕见。如《隶释》卷一《益州太守高眹修周公礼殿记》开篇就写道:“汉初平五年仓龙甲戌旻天季月修旧筑周公礼殿。”洪适指出:“献帝初平五年正月朔已改元兴平矣,此碑书九月事尚用“初平”者,天下方乱,道路拥隔,置邮到蜀稽晚也。”类似例证又有《隶续》卷三《建平郫县碑》:“建平五年六月郫五官掾范功平史石工[~符号~]徒要本长廿五丈贾二万五千。”洪适说:“建平者,哀帝之纪年,其五年已改为元寿矣,此云“建平五年六月”者,与《周公礼殿碑》相类,殆蜀道未知改元尔。”(〔宋〕洪适撰:《隶释隶续》,中华书局据洪氏晦木斋刊本1985年11月影印版,第17页,第305页)这是年代的错误。日期的错误,严肃的历史文献有时也难以避免。吴玉贵著《资治通鉴疑年录》于前人已经发现的《通鉴》纪时之误而外,又揭示出《资治通鉴》在纪事时间,特别是干支纪日方面的错误近900条。我们当然不能据此以为《资治通鉴》是伪书。吴著讨论“错误原因”列出8种情形,其中“因历法不同而误”和“因一时疏忽而误”两种(吴玉贵著:《资治通鉴疑年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7月版,第17页至第18页,第20页至第21页),对于石刻发现纪日文字“错误”的理解可以参考。
秦代的交通礼俗
秦出土文献所见选择时日吉凶的数术书《日书》中,多有涉及交通文化的内容。比如,表现“行归宜忌”的文字不仅数量可观,覆盖面大,其禁忌方式也备极繁密。睡虎地《日书》甲种可见有关迁徙禁忌的内容,如:“正月五月九月,北徙大吉,东北少吉,……”(五九正壹),向其他方向迁徙则多有不利。迁徙也是一种交通行为。《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11年),有人于华阴平舒道持璧遮使者,预言“今年祖龙死”,“使御府视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于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迁北河榆中三万家。拜爵一级。”卜问迁徙之吉凶的方式如果与睡虎地《日书》属同一系统,时在秋季,而北河榆中地当咸阳正北,其卜问结果当与简“五九正壹”一致。由此可以推知“迁北河榆中三万家”,其时当在九月。
秦始皇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游踪甚广的帝王,其政治实践特别重视“巡行郡县以示强,威服海内”(《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记载他平生凡8次出巡。其具体行期,则只有一例见于司马迁的记载,即《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这是秦始皇最后一次出巡。“十月癸丑”这个日子,在睡虎地秦简《日书》中属于秦人建除系统的“秦除”和“稷辰”中,皆未见与“行”有关的文字,而在可能属于楚人建除系统的“除”中则正当“交日”。而“交日,利以实事。凿井,吉。以祭门行、行水,吉”(四正贰),是利于出行的。“祭门行”仪式的意义,或即“告将行也”(《仪礼·聘礼》,郑玄注),“行水”则说水路交通。秦始皇此次巡行先抵江汉平原,“十一月,行至云梦”,很可能因此而据楚数术书择日。
另一方面,“秦除”“稷辰”虽未言“行吉”,但“十月癸丑”亦不是行忌日。属于秦人建除系统的“秦除”和“稷辰”中,均未见“行吉”日。据此或许可以推想,秦人有可能是将“不可行”日之外的其他的日子都视作“利以行”“行有得”或“行吉”之日看待的。这样,秦人的建除中虽不著明“行吉”之日,而事实上的“行吉”日却远较“楚人建除”为多。可见,事实确如李学勤所指出的,“楚、秦的建除虽有差别”,但“又有一定的渊源关系”(李学勤:《睡虎地秦简〈日书〉与楚、秦社会》,《江汉考古》1985年4期)。另一方面,当时占日之学流派纷杂,即所谓“四夷各异卜,然各以决吉凶”,而“齐、楚、秦、赵为日者,各有俗所用”(《史记·太史公自序》),重要的交通活动,大约需要事先综合考虑不同建除系统的出行宜忌。
秦发现刻石文字言“采药昆仑”,言“三月己卯车到此”,言“前□可□百五十里”,则“三月己卯”是一个与“行”有关的日子。我们在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禹须臾”题下看到这样的文字:“戊申、戊寅、己酉、己卯、丙戌、丙辰、丁亥、丁巳、庚子、庚午、辛丑、辛未,旦以行有二喜。”(一〇一背)可知在这套数术系统中,“己卯”日是有利于“行”的。
秦代的“徼外”交通
质疑“采药昆仑”刻石真实性的学者,多指出石刻发现地点超出了秦帝国的疆域,即秦长城的西端“临洮”。而《史记·秦始皇本纪》说“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地……西至临洮、羌中”。明确说到“羌中”。张守节《正义》:“《括地志》云:“临洮郡即今洮州,亦古西羌之地,在京西千五百五十一里羌中。从临洮西南芳州扶松府以西,并古诸羌地也。””郭涛这样的判断值得重视:“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在长城徼外的路线可以视为“羌中道”的组成部分,只不过比河湟道和婼羌道位置更要偏南,海拔更高,人员的流动也更少,因此鲜为人知。”(郭涛:《从交通地理角度看“昆仑石刻”》,《光明日报》2025年7月16日08版)米小强指出,《汉书·五行志》:“史记秦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长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见于临洮”,“是岁始皇初并六国,反喜以为瑞,销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内地秦人与“徼外”“夷狄”的交往,更早则有伯乐、九方堙为秦穆公“求马”,“得马”“沙丘”的故事。而后人多以“沙丘”对应敦煌“渥流”,理解其地在西北边(王子今:《论伯乐、九方堙为秦穆公“求马”》,《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2期)。而乌氏倮与“戎王”的交易,也可能远通“徼外”(晋文:《官商乌氏倮与正史记载最早丝路贸易》,《光明日报》2017年3月27日14版)。刘瑞列举秦封泥中所见“西方谒者”“西方中谒”“西中谒府”诸例,以为“秦设有司负责“西方”宾客,表明了秦与其统治区域以西之间的交往有相当规模”(刘瑞:《新见秦五大夫翳刻石初探》,《光明日报》2025年8月6日08版),论据是有说服力的。
秦军灭楚之后,“因南征百越之君”,事在灭燕、灭齐之前(《史记·白起王翦列传》)。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地……南至北向户”。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琅琊刻石亦宣称“皇帝之土”“南尽北户”。而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方才“为桂林、象郡、南海”(《史记·秦始皇本纪》)。南海置郡之前,秦“南攻百越”,“深入越”,“秦祸”“南挂于越”,“行十余年”(《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或说秦人“与越杂处十三岁”(《史记·南越列传》),都是在“徼外”活动。而徐巿船队海上远航,也突出体现了秦人对超出秦帝国疆域之远方的进取精神。
秦代的东西轴线
日本秦汉史研究学者鹤间和幸著文《关于始皇帝遣使“采药昆仑”石刻的发现》附图“利用卫星影像绘制的秦代南北、东西轴线”。所谓“南北轴线”以同样位于“东西轴线”上的“周洛阳城”为中心,北则“太原”,南则“荆州”。其“东西轴线”连接了这样几个地点:“黄河源石刻(扎陵湖)”——“秦西门(汧水)”——“秦咸阳”——“函谷关”——“周洛阳城”——“秦东门(朐县)”。论者写道,据“专攻卫星影像分析的惠多谷先生”绘制的“秦代的东西轴线”,““采药昆仑”石刻向东与始皇帝陵、洛阳城、秦东门(江苏省连云港)精准地呈现一字排列,堪称令人惊叹的奇观”。(《光明日报》2025年7月28日08版)
应当指出,惠多谷绘制的“秦代的东西轴线”,其实中国考古学者早在考察“通过西汉都城长安中轴线延伸”的“超长南北向建筑基线”时,已经向学界提示。1995年,秦建明、张在明、杨政在《文物》第3期刊发文章《陕西发现以汉长安城为中心的南北向超长建筑基线》,明确表示:“可以绘出一幅秦汉时期地理坐标图,这幅图的坐标点为长安城(或咸阳),其纵轴上方指向朔方郡,下方指向汉中郡,其横轴东方指向上朐秦东门(应为“朐东门”——作者注)。这个坐标系与今经纬坐标相较,轴北端偏西约1°,轴东端偏北约1°,轴南端偏东约30'。其纵轴较直,与横轴又相垂直,与今日子午卯酉坐标系有1°左右的逆时针偏转。这一现象很难仅以巧合揣度。”研究者推测,“秦汉时代在掌握长距离方位测量技术的基础之上,可能已初步具备了建立大面积地理坐标的能力。”所附“基线与秦东门”图,标示了以“秦咸阳”为交点与“纵轴”垂直的“横轴”,东达“秦朐县”。
如果确实存在这种“大面积地理坐标”,在作者提示的天齐祠、汉长陵、汉长安城中轴线等地标因素尚未出现时,秦咸阳北面沿子午岭修筑的直道与秦咸阳南面重要路段沿直河而行的子午道,其设计和施工或许与这种方向意识及空间观念有一定关联(王子今:《秦直道的历史文化观照》,《人文杂志》2005年5期)。鹤间和幸、惠多谷提供的“秦代的东西轴线”,向西延伸到“黄河源石刻(扎陵湖)”,并且指出““采药昆仑”石刻向东与始皇帝陵、洛阳城、秦东门(江苏省连云港)精准地呈现一字排列”称之为“令人惊叹的奇观”。这样的意见,也许可以为我们理解““采药昆仑”石刻”发现的意义,提供某种启示。
还应当指出,在秦建明等称作“横轴”,鹤间和幸称作“秦代的东西轴线”上,测知“秦咸阳”东距黄海岸边的“秦东门”约1000公里,西距““采药昆仑”石刻”约1037.5公里。而在高速路普遍开通以前的公路营运线路里程,咸阳至玛多1560公里,咸阳至连云港1052公里(《全国公路营运线路里程示意图》〔第二版〕,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6月版)。而甘青交通,特别是高原道路建设稍显滞后,也是可以理解的。
这样的里程数据,也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连云港和扎陵湖与咸阳“精准地呈现一字排列”的一东一西两个地点空间方位的大致对应关系。而秦始皇时代“采药昆仑”的可能性,也可以由此大略推知。